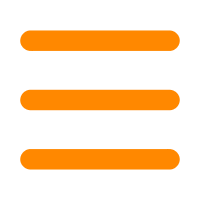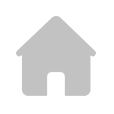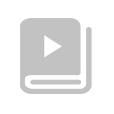假如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中国社会踏入近代已经一百六十多年了;
假如从1902 年清末修律算起,中国法律规范的现代化也已经一百年有余了。
百年回望,大家当然有理由为中国社会、为中国的法制而欣慰,从皇帝专制规范、《大清律例》到人民代表大会规范、《中国宪法》、《中国刑法》,大家可以明确的听到历史前进的脚步声。
但立足当今中国社会的现实,大家的心情或许就不那样乐观。由于:尽管根据现代理念建设的立法体系、司法机构已经基本健全,但现代“法治”的理想却非常难说已经大体达成。一个基本的表现是:权力超越法律仍然是弥漫在中国社会中的常见现象,全社会法律信仰的程度依旧非常低。以至于叫人不能不哀叹:一百年来,从根本上讲,中国依旧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回顾百年过去,中国法律走过了艰辛的经历;前瞻将来,中国法治的道路依旧并不平坦。
自人类15世纪进入加速度进步的年代,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讲,一百年无论怎么样都不可以算作一段短的时间。因此,无论是纵向和我们的过去比,还是横向和世界其他民族国家相比,大家有理由这么觉得:中国百年树法,本来应该更好。
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这要从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开端——晚清法律改革说起。
继1901年1月清政府决定“变法”、号召向西方学习之后,1902年3月清政府又决定“修律”,晚清十年的法律改革由此而始。一般觉得,清末十年的法律改革分为两个阶段,1902-1905年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法律改革主如果删削旧律,内容和工作不出张之洞、刘坤一《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范围;但自1906年7月清政府决定“仿行宪政”、推行“预备立宪”之后,清末的法律改革便进入第二阶段,开始向纵深进步,国家致力于打造新的法律体系、实行司法独立。其中,从1902年清政府决定修订《大清律例》,到1907年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上奏大清刑律草案,再到1911年《大清刑律》的颁布,刑事法律的变革贯穿了晚清十年法律改革的整个过程。
《大清刑律》是中国法律史第一部具备独立意义的现代刑法典,同时也是清末各种新法中拟定时间最长、争议最大的一部法律。自1907年十月3日(光绪三十三年8月26日)和12月30日(光绪三十三年11月26日),修订法律大臣、法部右侍郎沈家本分别上奏大清刑律草案总则和分则将来,对刑律草案的各种反馈建议便纷至沓来,其中以中央各部院、地方各督抚的签注建议最为要紧。正是在中央和地方大员签注的影响下,清廷下令修订法律馆会同法部对刑律草案进行修改并于1910年2月2日(宣统元年12月23日)颁布《修正刑律草案》。《修正刑律草案》与刚开始上奏的草案相比,总体布局由原来的总则、分则两部分便成了总则、分则和附则三部分;虽然总则17章、分则36章没变,但条文却由387条增加到409条,在篇章名字、条文内容上也多有变化,在总则、分则之后增加的“附则”五条更是原来草案所完全没的内容。《修正刑律草案》由宪政编查馆核查定稿后交由资政院审议,1911年1月25日(宣统二年12月25日)《大清刑律》颁布。
应该说,晚清十年的法律改革,其涉及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在中国法律史上是前所未有些。就立法内容而言,一个包含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诉讼法、法院编制法在内的全新法律体系已经初步打造。就立法过程而言,其它法律的拟定相对都比较顺利,唯独刑法典的拟定一波三折,1907年的刑法典草案不只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而且引发了绵延数年之久的“礼法之争”。这的确是一个值得仔细“咀嚼”的历史现象,但有一点,觉得反对刑律草案就是顽固、守旧的说法恐怕是站不住脚的,由于同步进行的其它法律的拟定也基本是移植和照搬西方的法律,就没引起这么大的风波。而且张之洞就说过,但凡传统法律所无或者基础薄弱的法律,如商法、民法、交涉律,可以尽用洋律。即便就刑法而言,决定对《大清律例》修订本身就是引进西办法律的过程,这一点一般建议是了解的,“于名教纲常礼义廉耻之重,仍以中律为主。其余中律所未完备者,参用洋律。为交涉事件等项,罪名可以纯用洋律,庶风土人情各得相宜矣”[1]。这表明,以张之洞为代表的礼教派并不顽固,他们了解取西方之长补中国之短的道理。但对传统法律中极为成熟和发达的刑法典,他们则当仁不让,对基本是移植和照搬西办法律的刑律草案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这一方面展示了他们对中国传统刑法文化的自信,期望藉此能有和西办法律文化平等对话的机会;其次他们也担忧,假如连这“最拿手”的东西都没和西方平等对话的资格和机会,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斟酌、融合中西岂不成了一句空话?即便今天看来,这的确也是个问题,正如苏亦工老师所言,“根据常理,清朝官方和沈氏个人如均以中西融合为宗旨,则拟定刑律时,传统法律资源中可供汲取者正多,又何必舍近求远,假手洋人呢?”[2]。愈加多的征兆和材料好像在证明,刑律草案对于中国传统刑法典中有价值的规定,并没可以非常不错的予以消化吸收而留存于新刑法典之中,而是“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并泼掉了”。下面以《大清律例》中关于官吏犯罪和暴力性犯罪规定的积极价值被《大清刑律》废弃为例,说明草案编纂者对“当地资源”缺少创造性转化借助。而怎么样正确处置当地原因和外由来素的协调融合问题,是中国法律近代化过程中的重点问题。对这个问题的重要程度、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是晚清刑事法律改革以来的中国法律现代化过程中的主要病因。
古时候吏员犯罪有公罪和私罪之分,且私罪的量刑比公罪为重。就法律条文而言,吏员的所有活动都纳入法律的规范之内,不但故意犯罪应受严惩,与职务有关的很多过失犯罪也一样惩处。刑律草案大幅度调整了对吏员犯罪的定罪处刑,如与职务有关的很多过失犯罪不再科刑,官员的渎职犯罪被严格限定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内,对官员贪污贿赂犯罪的量刑也大大减轻。对此很多签注提出了异议,如江西签注一方面觉得第一百六十四条聚众为暴行或胁迫罪中缺少对官吏人身的特别保护,“伤害实行公务之吏员,岂可与凡人同论乎?”;其次又觉得第二百三十五条吏员明知虚伪之事实而据以制作所掌文书图样罪中应规定过失犯罪处罚的条约,“吏员有办事之权,应负办事之责。如有申告虚伪之事实者,若不查是非制作文书,虽非有意舞弊而制作错误,亦应负其责任。况虚伪之事,所关甚巨。今本案定为吏员不坐,与理尚有未协,此条应行酌改”[3]。对于贪污贿赂犯罪,草案第140条仅定二三等以下有期徒刑,两广觉得旧律贪赃枉法之罪处刑甚严,可至死刑,草案量刑过轻,“将使墨吏罔知戒懼而苞且之事日多,似于吏治不无妨碍”,它还觉得草案第260条吸食鸦片烟罪官民无别不妥,应该重罚官弁而轻责平民[4]。湖广签注则对第一百四十五条关于告状不受理罪提出异议,觉得官员不受理举报,或许会导致极为紧急的后果,因而应予以严惩,“查现行律例告状不受理,如告谋反、谋叛不即受理掩捕,以致聚众作乱、攻城劫掠者处分甚严,所以杜萌乱而儆溺职。目前沿江一带,伏莽甚多,或倡言革命毫无顾忌,设或有以此等事情告发,不即受理捕治,致生厉害治安,实非浅鲜。本条罪仅四等徒刑而止,未免轻纵,似应酌量加重”[5]。但修正案对以上建议,均未采纳。
传统法律固然给予了官吏以各种等级特权和特别保护,但同时意味着比凡人愈加严格的需要和惩处,就此意义而言,传统法律下官员的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是相对公平的。草案根据近代法律精神,剥夺了官员的各种等级特权和特别保护,同时也放松了对他们的需要,单就法理而言,这是在一个新的意义上的平等和公平,未尝没道理。但揆诸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与现实,大家看到中国行政运作从来就和西方有着很大的差异,如政府一直是社会的核心,官员的权力非常大而事实上极少遭到行政法规的约束,假如再不在刑法上就他们的犯罪行为规定较为严厉的惩处,完全大概对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导致无可挽回的损失。而且纵览近百年来中国公务员的管理,官员的各种特权和特别保护事实上仍然存在,但比凡人愈加严格的需要和惩处却因法律的取消而取消,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利和义务的不平等和不公平。所以大家今天常常听到和看到的一些重特大事故,如重庆天然气井喷事件、陕西铜川陈家山煤矿瓦斯爆炸事件与触目惊心的假酒、假烟、假奶粉、毒火腿的横行,这其中事实上都有一个政府官员失职、渎职的问题,但却极少看到有政府官员为此承担责任,他们常常以不了解此事为自己开脱责任,这说明至少在法律上是有漏洞可钻的。以至于“一个私自成立,无任何办学资质和办学手续,学员无任何合法途径的‘三无’假军校,(在山西太原各有关主管部门的眼皮子底下公开)一办就是五年”,太原副市长范世康却说“学生让人骗也有自己是什么原因。一些学生、父母无知没办法,不根据有关招生的规章规范办事,片面听信一些人的花言巧语,结果上当被骗”[6]。呜呼,需要普通老百姓个个须有“火眼金睛”,那人民纳税“供养政府”又有什么用?这是大家最不愿到的。所以,《大清律例》中对官吏犯罪的规定是有价值的,它能有效的预防因官员渎职而产生的害处超出人民可以承受的范围。关于贪污贿赂的犯罪,海外发达国家的确极少用死刑来惩处,由于它被视为经济犯罪而性质不是特别紧急。但对于中国来讲,因为各种缘由,官员的此类犯罪不少,对社会的影响非常大,一直都是普通民众最恨之入骨的犯罪现象,不予以严惩就没办法保证最起码的社会秩序。所以直至今刑法里对于此类犯罪,仍有最高刑死刑的规定。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等到中国规范完善,此类犯罪现象降低,自可以与世界接轨,但在现在还不可以,那就更不需要说一百年前的中国了。很多签注强调对西方文化要取其利而避其害,后人或许该从中得到教训而不是不屑一顾[7]。
[1][2]下一页